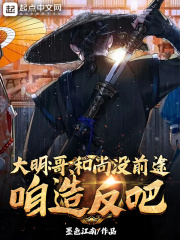王家老者脸色铁青,却被族中年轻人拉住低语几句,终是咬牙点头。
一场风波,竟由此止。
朱标叹道:“社,不必权,也能理。”
朱瀚不语,直至众人散去,才低声道:“这社,是棋盘上的子,而你,要做落子之手。”
陈鹤鸣在后,忽然问道:“王爷可愿指我——什么叫落子?”
朱瀚背影如山:“落子者,不必出手,但一念之间,可定生死。你如今学下棋,可知这落下的,不只是子,是命。”
当日夜,朱瀚独自坐于社庙中后檐,默然饮茶,忽听耳畔系统之声响起:
【叮!签到成功!获得奖励:“青锋志”技能,效果:可洞察人心利害,三言之内观其志向。】
朱瀚微微一笑,眸光幽深如墨。
“系统,你说这‘青锋志’可用来看谁?”
系统寂然无声。
东宫后院,梅花初绽,枝头红白相映。
朱瀚与朱标对坐石桌,面前摆着一盘棋。
朱标执白,朱瀚执黑。
棋局正酣,朱标忽问:“皇叔既设三局,那书局之中,所推何学?”
朱瀚未应,提子而下,一声轻响,黑棋咄咄逼人。
朱标看了看棋盘,皱眉:“皇叔此步,是弃角攻心?”
朱瀚淡然:“角为势,心为形,弃之可得局。”
“若弃太多,形散神疲,终难久持。”
朱瀚这才抬头,眸中浮起一丝笑意:“所以此局,只能由你来守。”
朱标一怔,随即点头:“那便请皇叔将‘书局’之法一一道来。”
朱瀚不言,抬手一挥,身旁早有内侍取出一卷,徐徐铺开。
上面列有“通典、通论、通讲、通录”四纲十目,每一目后皆详注数百字,文理缜密。
“我将书局命名‘通文社’,通者,贯通;文者,文心也。以太学为本,延伸至各府州县书院,凡入社者皆受‘四纲十目’所教。”
朱标翻看细读,目光渐亮:“以儒入文,以史佐义,以礼导心,以志存忠。皇叔此法,兼容并包,既承古道,又可开今局。”
朱瀚却摇头:“你只看其广,却未见其深。”
“何意?”
“通文社非仅为教书,更在筛人。”朱瀚缓缓道,“社中每岁设‘文心三题’,从中拣出志士、贤才、能吏,入人局、行局。”
朱标抬头,神色微变:“皇叔此举,已近‘择官’。”
朱瀚淡然一笑:“若你不欲择官,那这天下迟早有人替你择了。”
朱标沉默片刻,才低声问:“此事,父皇可知?”
朱瀚放下棋子,回身道:“你父皇只看结果,不问手段。”
朱标苦笑:“你倒是比他更像朱元璋。”
“我若是朱元璋,你已不在东宫。”
朱瀚淡淡道,“你还太嫩,太仁。仁者可养天下,未必能治天下。”
朱标倏然起身,负手而立:“皇叔所设三局,皆为我谋。我怎能不感?可若太过用力,终非社学,而是私学。”
朱瀚走近一步,盯着他的眼:“你既有此虑,便更要慎选人。那陈鹤鸣,可堪一用?”
朱标沉吟片刻:“他志气有余,锋铓太露。可堪为一枪,不堪为一盾。”
朱瀚微微一笑:“你倒看得清。”
“我毕竟不是你。”朱标语气平静,“不能凡事以胜负计。”
朱瀚凝视他良久,忽而一叹:“但愿你这份仁心,不被世道消磨。”
次日,东宫传召通文社试讲,诸生集于太学西堂。
陈鹤鸣亦在其中,眼神沉静,不卑不亢。
讲台上立一人,青衣,束发,手执竹简,正是朱瀚所选“书局讲使”——章惟中,原为翰林修撰,才学通达,气度翩翩。
他手拍简面,淡然启口:“今日一题,‘为君之道,在于宽仁乎?在于刚决乎?’诸位请论。”
诸生哗然,有人低语:“此题分明指东宫。”
“正是,若答‘宽仁’,恐为阿附;若答‘刚决’,又恐忤上。”
“此题锋利,非得其道,必被记恨。”
陈鹤鸣却面不改色,起身拱手:“学生愿先答。”
章惟中点头:“讲。”
陈鹤鸣步上讲台,目光一扫:“宽仁与刚决,非对立也。仁者不以义废法,决者不以情灭理。为君者,当知何时宽,何时断,此之谓‘权衡’。”
他顿了顿,沉声道:“东宫仁厚,行事有度,非宽之误;若辅之以法以才,以忠直之臣佐之,则仁中有骨,柔中有刚。君不独为决断者,亦为容众者。”
章惟中点头,神色未动,却在笔记上一笔重画。
台下诸生低声议论:“此言进退有据,不露锋芒,实为妙言。”
陈鹤鸣讲罢而下,朱瀚于帘后默然注视,眼中多了几分赞赏。
“此子可为‘行局之用’。”他低声对一旁随侍言道,“让他入京职坊署,主文案调理,再以三月察其行。”
三月后。
东宫内,朱标再召朱瀚,眉目间多了一份从容。
“皇叔,那三局已成雏形,文社初开,人局正整,行局亦渐显绩。”
他手捧册卷,“通文社收录三州三十六人,皆可用之才。”
朱瀚略一点头:“通则必散,散而后聚。下一步,你当亲临其地。”
朱标一愣:“亲自出京?”
“是。”朱瀚指地图一角,“去洛阳、去曲阜、去雁门。洛阳是天下文脉之根,曲阜是儒门正统之源,雁门则人多读书、世代清白。你若能与三地学子晤言讲理,便是真正得人心。”
“可父皇……”
“你父皇若知你志在天下,而非一宫之地,必喜而纵之。”朱瀚眸中浮光暗动,“但他不会给你多长时间。”
朱标沉声道:“三月之内,我必归京。”
朱瀚看着他,眼中忽然柔了些:“朱标,我愿你出走一遭后,能真正明白:你不是因为是太子才得人心,而是因为你配得上太子这个位置。”
数日后,金陵风暖,御街花开。天未明,朱瀚便立于望江楼前。
他神色平静,眸子深邃,宛如江水之底的潜流,不言语,却动人。
忽有脚步声急,陈鹤鸣快步而来,手中捧着一卷文稿,气息略显急促,拱手跪下:“王爷,社中有急报。”
朱瀚未接,只道:“念。”
陈鹤鸣展开卷轴:“曲阜论道甫毕,太子南行途中,于寿州停驻,与当地主簿夜谈政务三更。翌日,百姓跪迎五里之外,自发筑道石以示心诚。”
“百姓筑石?”
“是。原为小民捡河石铺道,一夜成路。有人在石上书‘愿太子再过吾门’。”
朱瀚听罢,脸上没有太多波澜,只淡淡点头:“如此便好。”
陈鹤鸣迟疑道:“王爷,是否应趁势入奏?”
“不急。”朱瀚转身缓步入楼,“朱标行的是名望之道,若我这时代言,反显其力非己有。且看百姓之口如何传,学宫如何议。”
陈鹤鸣低头,不再多言,却越发佩服眼前这位沉如山岳的王爷。
望江楼中,一张案,一壶茶,一盘旧棋。
朱瀚将昨日未尽的棋局缓缓铺开,目光落在棋盘中间那枚孤子上,沉吟许久,自语道:“人心是水,顺流可行舟,逆流可夺势。”
他将一子轻轻落于边角,笑意浮起:“朱标,你这一子,确是妙。”
与此同时,曲阜东门。
朱标踏着晨光出行,身后不随侍卫,只一介随行学士,淡衣短冠。
他走入街中,行过茶肆、书铺、工坊,不时有人向他微颔、作揖。
他未言语,只微笑点头,一步不停。
直至一座低矮书屋前,他停下,抬头望着匾额——“纸上山”。
他推门而入。
书屋内一老者正在理书,见他进来,未多惊讶,只拱手道:“殿下来早了。”
朱标拱手回礼:“先生信我真会来?”
“纸上山虽小,但藏天下之声。你若不来,便枉得民心。”
老者名为柳观松,曾任曲阜学署掌教,因言直辞退,今隐于市中开书屋。
朱标数日前曾夜访其庐,二人对谈数时,今日约再见。
朱标坐下,轻声道:“昨日我过亭坊,见孩童争抄一文,问之,乃是先生所写‘问心篇’。”
“那不过是些老生常谈。”
“可孩童能诵,便非寻常之言。”朱标目光灼然,“我想请先生入‘通文社’,为教纲主笔。”
柳观松未应,低头拭书,良久方开口:“太子真愿我入社?”
“我愿你入,不为名声,只为社中多一根梁。”
柳观松抬眼盯他,目光沉如水井:“你知我之言,有时不合朝意?”
“我不求你合,只求你真。”
“若我言之所向,有违太祖旧旨?”
“那便由我担。”
柳观松缓缓起身,行至窗前,推窗望天,一轮旭日刚跃出山头。
“太子若有此心,老夫便拂尘再登讲台。”
朱标起身一礼,庄然道:“他日若社成学宫,纸上山当为社中正讲之所。”
柳观松转头,笑道:“你许我此诺,便须守之,莫让此山再被火封。”
朱标点头:“我守。”
傍晚。
朱瀚在府中独坐,案头一页书简,正是通文社传回朱标曲阜之行的详细记录。
随侍欲进,见他眉目平静,便退而不扰。
忽然门响,有人快步入内,是他旧部吴深。
“王爷,京中近日突有新风——”
朱瀚未看他,只道:“说。”
“太学中一位年青讲书郎,讲《大学》时自加批注,提出‘君权当问民意’之说,引动轩然。原是通文社中人。”
朱瀚终于抬头:“他叫甚名?”
“林文绩。”
朱瀚缓缓点头:“这个名字,我记得。”
“王爷不忌?这般言辞,终究过烈。”
“若有人敢讲,便有人敢听。”朱瀚起身,负手而立,“你只看他言烈,我却看他能聚心。世间百姓未必知义理,只知有无听他说话之人。”
吴深沉声道:“如此言论,陛下若知……”
朱瀚眼神冷峻:“他若知,只看结果。”
吴深一怔。
“你记着。”朱瀚忽而转身,语气低沉而有力,“扶太子者,不在于立他于高,而在于众心可托。若今日有人愿为太子说一句话,哪怕那话不中听,也要护着他说下去。”
吴深默然,拱手退下。
夜深,京师太学。
通文社内,一众学子正围灯夜讲,灯火摇曳,映着他们年轻而执着的眼神。
林文绩正与几人辩论,他指着墙上一幅图道:“君者,上也;民者,根也。若无根,何以挺立?”
有生问:“可若民误,岂非误君?”
林文绩答:“君以权导民,民以言正君。若上不察下之言,则高楼必倾。”
众人沉默片刻,忽有一人低声问:“你敢说这话,是因有王爷庇你罢?”
林文绩静了静:“我不是因王爷才敢说,而是因为王爷听我说了,还让我再说。”
“你不怕?”
“怕。”他眼中闪光,“但若连说话都怕,这世道,便真没救了。”
长安街头,春风已暖,御马监的钟声清脆,钟响三更。
朱瀚却仍未就寝。
他独坐书房,案前摊开一幅幅京城商贾出入、书肆流转的账目图纸,每一页都细致到极致,连最不起眼的茶摊位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“王爷。”陈鹤鸣捧着热茶进来,小声道:“夜深了,歇息罢。”
“坐。”朱瀚未抬眼,翻动一页,“夜才正浓,梦该从此始。”
陈鹤鸣心中一凛,小心坐于一侧。
“太子那边,有何新讯?”朱瀚话音平静,却藏着雷霆。
“回禀王爷。”陈鹤鸣低头,“通文社三日前设讲坛于弘文馆外,太子以学子之身,与众生共论‘慎言’。众人称其‘能听民语,知慎权者也’。”
“弘文馆之外?嗯……此地一旁便是贡院,百名举子聚于一处,太子这一步,落得漂亮。”朱瀚轻声言语,眉梢却有一丝赞许。
他手指轻敲桌面,停了许久,忽然道:“让人备轿,我要入市。”
陈鹤鸣一愣:“王爷此时……”
“此时最真。”朱瀚站起身,换上一袭素色长衫,“夜市之人,话最多,情最实,若要扶朱标,不能只听士林书生,也须知百姓肚肠。”